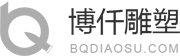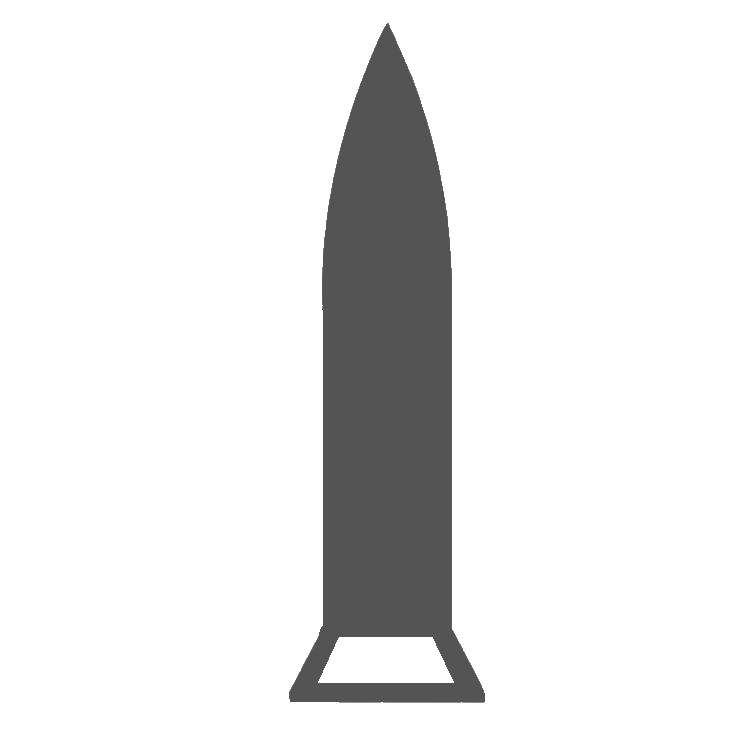有位朋友說:“民族形式問題,現在不是理論而是實踐問題。”我體會到“寫意”是我們民族的藝術特色之一。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凡是好的藝術都是既有客觀因素,又重視主觀因素。既有“再現”因素,又有“表現”因素,我們中國的古代畫論高度概括了這一藝術創作的辯證關系,叫做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我想,“藝術”主要解決人們的“情感”問題,而不是解決對世界的科學認識。
所以人稱“美學”是情感的科學,我覺得藝術家就是以自己的“真情實感”,自己的特殊“體會”來補充人們的不足。人們看一件藝術品也決不會想從中得到物理化學方面的道理,而是想更深地領會宇宙人生的美好,更懂得人們的悲傷和歡樂,更好地去領受這短暫而豐富的人生。因此,藝術是藝術家自己對字宙人生的經驗和體會的凝結,藝術的價值其實是這些“體會”的價值,當然,這些“體會”要得到高技巧的表達。
但歸根結蒂是這些“體會”本身的價值,沒有深刻獨到的“體會”,那么,什么技巧都是沒有用的。而“體會”當然只有在社會實踐中來。在人們各種各樣的社會實踐中自會產生可歌可泣的感受,而藝術家與平常人不同之處就在于“歌”“哭”以后,還要反復咀嚼自己的痛苦和歡樂,然后加以表達,使之與人們共享,使之成為永恒。這種“感受”和“體會”,這種“靈魂”的提煉和升華就形成了我們中國人所謂的“意”。我們說要“寫意就是要緊緊抓住這種“意”而寫之。我們和主觀唯心論者的不同,就在于我們知道,這“意”的來源是作者的生活實踐。我們和機械唯物論者的不同就在于我們深深懂得藝術的核心是我們在生活中實踐中所產生的“情”,所產生的切身“體會”,是提煉和升華的意”,而非客觀生活本身。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李解有兩首詠梅詩:“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
”上句說的是生活本身,也就是人們一睜眼就接觸到千萬朵在自然界生長的梅花,那只是生活的映象,而不是藝術。而第二句是你對其中兩三枝產生了特殊的感動,開始了“賞心”。使之所以在千萬朵中選擇了這兩三枝,當然是和你的全部經歷和心理有關。譬如,我就喜歡大雪重壓下幾枝壓彎了的梅花,而有人喜歡一大堆艷過桃、李,勢如火燒的梅花。這原因很簡單,我一直老挨批判,有人一直飛黃騰達,如此而已。所以這“心”之所以賞,就是“情之所鐘”就是“意之所寄”。就是藝術活動的內核,如果你把這“賞心之所”“動情之處”“寄意所在”,以高超技巧寫了出來,那就是“寫心”就是“寫意”就是“抒情”,就是藝術創造了。
我們的“寫意”為的是和以“寫實”為主的傳統大不一樣的。因為是“寫意”所以就不拘泥于一鱗一爪的繁瑣刻畫、就能緊緊抓住自己感動的核心,抓住自己“體會”到的要點,就能“要言不煩”“針見血《游園驚夢》中杜十娘《思春》一折,舞臺上只放一張桌子、一個瓶子、插一枝楊柳,而使人覺得春意盎然。我看過外國的歌劇,也表現春天,可又是陽臺,又是常青藤,又畫滿有玫瑰、薔薇之屬,還畫上茄子飛翔等。和中國布景一比,那“寫意”“寫實”的區別就判若天壤了。“寫意”的另一優點就是自然而然地加工。
正因為“寫意”所以就必然會予以強調、突出,甚至加以重新組合,加以大膽地“改造”,就能擺脫實物的局限和制約,就能得到藝術創造的大自由。王石谷(清代“四王”中最好的一位)說士大夫畫和俗工畫的區別就在于“寫”字。這“寫”就是強調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多于模仿客觀現象。就是要像書法一樣地“寫”,就是強調“表現”因素,就是要“寫意”地“寫”出,而不描摹皮毛現象。我在這里必須再補充的即是,我所說的“心“情”“意”都離不開生活實踐,都來源于生活實踐,最后還要回過來指導并改善人們的生活實踐,(包括作者自己在內)。
我們主要強調“記憶畫法”,所謂“靜觀默察,嫻熟于心,凝神結想,一揮而就”。我們也要寫生,但實際上只是參考而已,或者作為創作之前的準備工作,作為創作之前的研究資料。記憶畫,是從生活到藝術的最自然、最簡捷、最有效的途徑。
老畫家關松房先生說“我決不畫速寫,更不帶照相機,你們怕忘,我則盡情忘,以后還怕不忘,我一定要讓自己忘,要到幾年后實已忘不掉的東西,畫將下來就行了。”他是強調“忘”的重要,其實還是強調記憶法,只是說明了“忘”在記憶中的重要功能。我們為了便于“寫意”,便于記憶,又采用了各種“程式”的學習。廣東佛山的劉傳先生講了他學習的經驗,有一個十字口訣:“由、甲、申、田、園、王、國、日、用、風。”說的是:把人物的各種面貌先加以類型化,變成一種最易記憶的“程式”,然后,在此基礎上結合具體的 個性特點,加以深入刻畫。
作為記憶現實的輔助,作為藝術地概括現實的一個過程,一個階段,都不失是種“拐棍”,是可取的。天津泥人張,積數代人的經驗,整理出七十多種面模。他先和人們在茶館聊天觀察,然后回家找到類似的面模,再去面對真人加以調整加工。我認為這些都是在“寫意”為主的大體系中概括現實,幫助記憶的有效方法。而這種方法在“寫實”的體系中就失卻意義,因此也就無人采用和提倡了。由此可見,我們的“寫意”傳統是從訓練到創作的一整套體系,而且在國畫領域內已經形成主流,而在雕塑領域內則亟待整理、恢復和提倡。